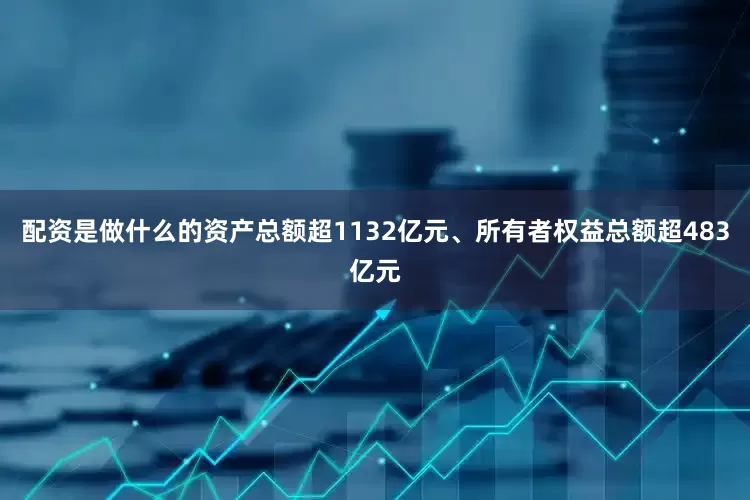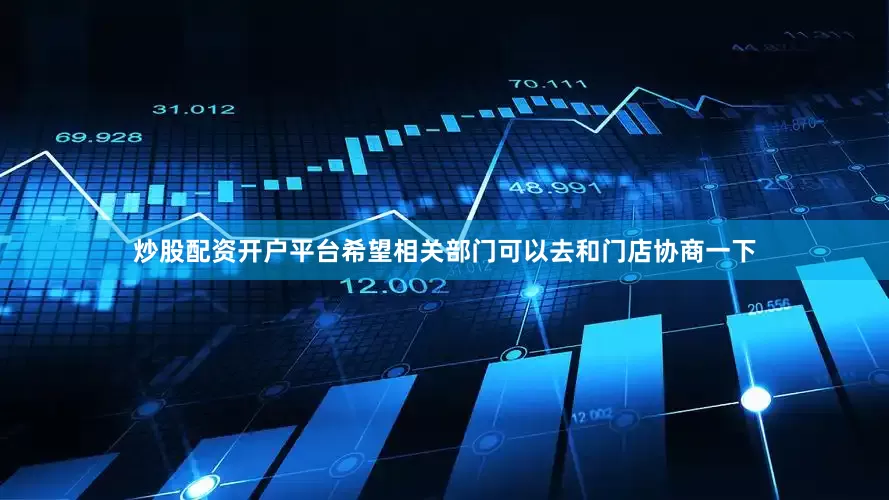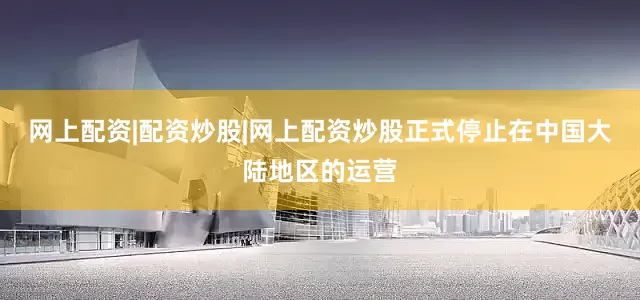十年动乱后最先公开否定文革的不屈灵魂,95岁高龄坦然告别人世
声明:本文根据大量史料文献及亲历者回忆整理而成,在保证重大历史事件准确性的前提下,对某些细节做了文学性表达。
时光荏苒,当我翻开父亲留下的那些泛黄日记时,往事如潮水般涌来。那个在乱世中坚守信念的老人,用他95年的人生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真正的风骨。
那是1976年深秋的一个下午,政协会议厅里静得出奇。当时社会上还弥漫着"两个凡是"的浓厚氛围,大家都小心翼翼地说话。就在这种沉闷的气氛中,坐在角落里的老父亲突然举起了手。
会议主持人有些意外,毕竟老人家已经很久没在公开场合发言了。「请梁老发言。」
父亲慢慢站起身来,声音虽然不大,但字字清晰:「各位同志,刚刚结束的那场运动,我觉得有必要说几句心里话。这场运动把我们国家折腾得够呛,究其根源,就是我们做事不按章法,全凭个人喜好决定一切。」
会场里顿时鸦雀无声。要知道,当时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还没开始,敢这样直言不讳的人实在太少了。
我记得那天晚上,父亲回到家后,母亲担心地问:「老梁,你今天在会上说的那些话,会不会惹麻烦?」
父亲摆摆手:「该说的话总要有人说,再说我这把年纪了,还怕什么。」
两个同龄人的初相识
说起来真是有意思,父亲跟那位伟人竟然是同年出生的。1918年的时候,两人在杨怀中老先生的家里第一次碰面。那时候父亲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当讲师,而那位后来改变中国历史的人,还只是北大图书馆的一个普通管理员。
父亲后来经常跟我们说起那次见面:「当时看这个年轻人话不多,但眼神很有神,总觉得他不是池中之物。」
1938年,父亲专门跑到延安去,在那黄土高坡上待了整整16天。期间跟那位领袖有过多次深谈,其中有两次竟然聊了整整一夜。

「我们俩都是湖南人,脾气都有点倔,但聊起天来特别投机。」父亲回忆时眼中总是闪烁着某种怀念的光芒。
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1月,在那位领袖和周总理的再三邀请下,父亲从重庆来到了北京。那位领袖还特意邀请他到家里做客,专门派了汽车去接,还亲自安排晚饭。
得知父亲吃素后,那位领袖哈哈大笑:「好,今天我们全家都吃素,这叫入乡随俗!」
听说父亲还寄住在亲戚家里,他马上让秘书安排,把父亲安置在颐和园里的一个清幽小院。
那段时间,两人来往密切,经常深谈到深夜。有时候观点一致,相谈甚欢;有时候意见不合,也会争得面红耳赤。也正是这种不分上下的朋友关系,为后来的那场著名冲突埋下了伏笔。
那场改变命运的辩论
1953年9月,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在京召开。会议期间,周总理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重要报告。在小组讨论环节,父亲的一番话如同一颗重磅炸弹,炸得整个会场为之震动。
父亲站起来,语气平和但内容尖锐:「诸位同志,我想说说自己的一些看法。过去30年革命,咱们党主要依靠的是农民兄弟,根据地也都在农村。可是进城以后,工作重心全都转向了城市,那些从农村出来的干部也都涌入城市,农村就显得空荡荡的了。」
他停顿了一下,环视了一圈会场:「特别是近几年来,城里工人的日子越过越好,可农村的农民依然过得很艰难。于是到处都有农民往城里跑,城里容纳不下,又把他们往回赶,这就形成了尖锐的矛盾。」
这番话说完,会场里的气氛立刻变得紧张起来。那位领袖的脸色明显不好看了。
在随后的发言中,那位领袖毫不客气地反击:「刚才有同志对我们的总路线提出了不同看法,认为农民生活太苦,主张要多照顾农民。这恐怕是想效仿古代圣贤搞什么仁政吧?」
「不过同志们要明白一个道理,仁政有大仁政和小仁政之分。照顾农民算是小仁政,发展重工业、对抗帝国主义侵略才是大仁政。只知道小仁政而不懂大仁政,那就是在客观上帮助了敌对势力。」
「更可笑的是,有人竟然在这里班门弄斧,好像我们这些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的人还不了解农民似的!我们今天的人民政权,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在根本利益上是完全一致的,这个联盟的基础是神圣不可侵犯的!」
接下来的几天里,会议对父亲的言论展开了猛烈批判。面对排山倒海般的批评声浪,父亲那股湖南人的倔脾气又上来了。他不顾一切地要求发言,结果在会场上跟那位领袖发生了激烈争吵,直到有人在台下大喊「梁漱溟给我滚下去!」这场惊心动魄的辩论才被迫结束。
事后,那位领袖为父亲的问题定了调子:虽然观点「错误」,但不算是敌对分子;需要批评教育,但也要给改正机会。
30年后,已经90岁高龄的父亲回忆起这段往事,语气中充满了复杂的情感:「当时确实是我处理不当,说话太直接了,让他在那么多人面前很难堪,特别是伤了老朋友的面子,这是我的不对。」
「不过话说回来,他当时的某些话也确实有些偏颇,就像我的发言也有不够准确的地方一样。这些都是人之常情,可以理解,没什么大不了的。」
「现在他已经不在了,我心里总感到一种深深的孤独...」

在风暴中选择沉默
那场著名的争论之后,父亲开始深居简出,在公开场合很少发声。1956年11月,正值「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」的热潮期,许多朋友都劝他出来说话,认为这是个好机会,可以把憋在心里的话痛快地说出来。
但父亲很冷静,他对我们说:「现在形势还不明朗,还是先观察观察再说。」
结果证明父亲的判断是对的。在随后的反右运动中,那些急于表态的朋友们大多遭了殃,被戴上了各种帽子,而父亲却平安地躲过了这一劫。
1966年,更大的风暴来了。「文化大革命」的狂潮席卷全国,任何人都无法置身事外。父亲也难逃厄运,家被抄了,不得不搬到北京鼓楼附近一个铸钟厂的两间破房子里居住。更莫名其妙的是,他居然被补戴了一顶迟到的「右派」帽子。
我记得抄家那天的情景。红卫兵小将们气势汹汹地冲进家门,把父亲几十年收藏的书统统装车拉走,连同那些珍贵的手稿一起。看着那些承载着无数心血的文字被人如垃圾般处理,母亲忍不住掉下了眼泪。
但父亲却出奇地平静。他拉着母亲的手说:「别难过,书没了可以再买,手稿没了可以重写,只要人还在,什么都有希望。」
扫街中的哲学思考
搬到铸钟厂的破房子里后不久,父亲就被安排到街道上扫地。对于一个曾经在最高学府任教、与国家领导人激烈辩论的哲学家来说,这无疑是巨大的反差。
但让我们全家都意外的是,父亲不但没有怨言,反而把扫地当成了一门学问来研究。
他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每天的「工作情况」:
「8月28日,天气晴朗。今日开始参加街道劳动,负责清扫新街口南大街一段,长度约为200米。通过仔细观察发现,路面落叶以梧桐为主,偶有国槐叶片。路人丢弃的废物中,香烟盒最多,其中'大前门'牌占绝大多数。扫帚重量适中,连续使用两小时后右手会感到轻微酸痛。中午休息时与同组工友老刘交流,得知其原为某工厂财务人员,为人忠厚老实。」
我看到这段记录时真是哭笑不得。我对父亲说:「爸,您这哪里是在扫地,简直是在做社会调查研究!」
父亲哈哈一笑:「儿子,生活处处皆学问。即使是扫地,也能从中悟出许多道理来。」
果然,没过几天,父亲就在日记中写下了他的「扫地心得」:
「连日来参与街道清洁工作,颇有感悟。其一,清晨时分街道最为洁净,正如人心,晨起时最为纯净;其二,垃圾虽多且杂,但若分门别类处理,便可化繁为简,治理国家亦当如此;其三,行人匆忙,鲜有人注意我们的劳动,这正印证了'功成不必在我'的道理。」
读到这里,我真是既心疼又敬佩。在那样艰难的境况下,父亲居然还能保持如此豁达的心境,还能从日常劳动中参悟人生哲理。
与此同时,父亲在政协机关的处境也变得微妙起来。有些人对他避而远之,生怕沾上麻烦;有些人则暗中表示同情,偶尔会主动打个招呼。这种人情冷暖,父亲在日记中也有记录:
「9月2日,阴天转晴。今日扫地时偶遇政协小王,其见我后立即转身离去,想必有所顾虑,可以理解。下午回家途中又遇老张,彼不但主动问候,还悄声询问我的身体状况。世态人情,一日之内便可窥见全貌。人心向背,本就如此变化无常,无需过分在意。」

批斗会上的坚守
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,父亲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。除了日常的街道清扫工作,他还要定期参加各种「学习班」和「批斗会」。但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,他也没有放弃自己的原则和底线。
有一次批斗会上,一个年轻的造反派指着父亲大声质问:「梁漱溟,你到现在还坚持你那套反动理论吗?还认为自己是对的吗?」
面对这种咄咄逼人的质问,父亲沉默了很久。会场里静得连掉根针都能听到。所有人都在等待着他的回答。
良久,父亲缓缓开口:「年轻的朋友,我的学术观点可以讨论,甚至可以批评,但请不要侮辱我的人格。」
这句话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。台下有人大喊:「你还敢嘴硬!还不老实交代!」
父亲依然平静地说:「我不是在嘴硬,我只是在坚持一个读书人应有的尊严。真理可以辩论,但良心不能出卖。」
这番话更是火上浇油。会场上顿时乱成一团,各种口号声、谩骂声响成一片。但父亲始终站得笔直,眼神坚定,仿佛一棵历经风雨却依然挺立的老松。
会后,我们都为父亲的安危担心不已。但他回到家后,居然还有心情在日记中写道:「今日会上争论激烈,然吾心如止水,波澜不惊。想起孟子之言:'居天下之广居,立天下之正位,行天下之大道;得志与民由之,不得志独行其道。'虽身处逆境,但初心不改。」
读到这里,我的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。在那样的环境下,父亲依然能保持如此的定力和气度,这需要多么坚强的意志力啊!
意外的转机
更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是,就在那次激烈的批斗会后,居然出现了一个小小的转机。那个平时对父亲最凶的红卫兵小将小李,竟然悄悄来到我们家。
那天晚上,小李红着眼圈对父亲说:「梁老,昨天会上的事...我觉得有些过分了。」
父亲看着这个年轻人,脸上露出了慈祥的笑容:「小李,你们也是身不由己。这个时代太复杂了,你们年轻人很容易被裹挟进去,不要为难自己。」
「可是...」小李欲言又止。
「没有什么可是的,」父亲拍拍他的肩膀,「你能有这样的想法,说明你的良知还在。这就够了。人总是要成长的,经历一些事情后自然会明白什么是对的,什么是错的。」
从那以后,小李对父亲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转变。他不但不再参与对父亲的批斗,有时候还会偷偷给他带一些食物,或者帮他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。
父亲在日记中记录了这个变化:「小李今日又来拜访,态度较前大为改观。与其探讨读书心得,彼深有感触。年轻人天性纯良,只是一时受到蛊惑,若能以真诚待之,必能唤回其本心。教化之功,非一朝一夕可成,但只要有耐心,终有开花结果之日。」
更有趣的是,小李开始向父亲请教学问。起初只是好奇地问一些关于孔子、孟子的问题,后来竟然真的对传统文化产生了兴趣。
有一天,小李问父亲:「梁老,您真的认为孔子的那些话都是对的吗?」
父亲笑着回答:「孔子也是人,当然不可能什么都对。但他教给我们的做人道理,比如仁义礼智信,这些基本的道德准则是不会过时的。你们现在批判传统文化,但人总得有些基本的道德底线吧?没有了这些,社会就会乱套的。」
小李被问得哑口无言,但显然是被说服了。从那以后,他经常来找父亲讨论各种问题,从哲学到历史,从文学到人生,无所不谈。父亲也很高兴有个年轻人愿意和他交流,经常到深夜还在谈论不休。
最黑暗时刻的坚持
1967年春天,文革进入了最疯狂的阶段。武斗频发,社会秩序几乎完全失控。在这样的大背景下,父亲再次被推上了风口浪尖。
这一次的批斗会规模空前,会场设在体育馆里,台上台下黑压压一片人头。巨大的标语横幅从屋顶一直拉到地面,各种革命口号声震耳欲聋。
74岁的父亲被推上主席台,面对着几千双愤怒的眼睛。主持会议的人通过麦克风大声宣布:「今天我们要彻底批倒批臭反动学术权威梁漱溟!」
台下立刻响起了排山倒海般的口号声:「打倒梁漱溟!」「砸烂旧思想!」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!」
面对这种阵势,许多人早就吓得腿软了。但父亲依然挺直腰杆站在那里,眼神清澈,面色平静,仿佛周围的喧嚣与他无关。
批斗进行了整整三个小时。各种各样的人轮番上台,对父亲的思想和人格进行无情的攻击。有人要求他跪下认罪,有人要求他彻底否定自己的过去,有人甚至提出要把他游街示众。
但父亲始终一言不发,只是静静地站着。当主持人要求他表态时,他缓缓开口:「各位同志,我的学术观点可以讨论,可以批评,但我不能昧着良心说话。一个读书人,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。这个底线我不能突破。」
这番话如同在炸药桶里扔了一根火柴。会场上顿时乱成一团,有人冲上台企图强迫他下跪,有人挥舞着拳头要动手,还有人大喊着要当场「解决」他……
在一片混乱中,父亲依然岿然不动,仿佛一座经历了千年风雨的古塔,虽然外表已经斑驳,但基础依然坚实。
最后还是小李和几个年轻人冲上台,以维护秩序为名把父亲保护了起来。在他们的护送下,父亲才得以安全离开会场。
当晚,父亲在日记中写道:「今日大会,场面虽然激烈,但吾心依然平静如水。想起古人所言:'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,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。'虽然身处险境,但道心不变。人生在世,总要为一些东西坚持到底,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。」
「批林批孔」中的独特声音
1972年底,全国掀起了「批林批孔」运动。作为研究传统文化的学者,父亲自然成了重点对象。政协组织了专门的学习班,要求父亲参加学习并表态。
在将近一个月的学习过程中,父亲始终保持沉默,无论别人怎么启发引导,他就是不开口。终于有人按捺不住了,公开指责说:「梁漱溟与孔子有着割不断的阶级感情,所以不愿意批判!」
这句话终于激怒了父亲。在随后的一次学习会上,他主动要求发言,用了整整两个半天的时间阐述自己的观点。
「同志们,关于这次运动,我有几点看法要说。」父亲站起来,声音虽然不大,但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坚定。
「第一,批林我赞成。林彪搞阴谋活动,妄图夺取最高权力,这确实应该批判。但是,我不批孔。」
会场里顿时议论纷纷。有人小声嘀咕:「他果然还是要为孔子辩护。」
父亲继续说道:「批孔是从批林引申出来的,但我实在看不出林彪和孔子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。一个是两千多年前的思想家,一个是现代的野心家,两者风马牛不相及。所以我不能违背自己的理性去批孔。」
「至于批林,我认为林彪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政治路线或者理论体系,他就是一个纯粹的野心家,一心想要搞政变夺权罢了。把他说成是什么理论家、政治家,反而抬高了他。」
这番话一出,整个学习班都炸了锅。从那以后,批判的矛头立刻转向了父亲。从1974年2月到9月,整整6个月的时间里,几乎每天都有针对他的批判会。
但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组织者最后问他有什么感想时,父亲的回答。他一字一句地说:「三军可夺帅也,匹夫不可夺志也。」
这句话传开后,在知识分子圈子里引起了巨大反响。许多人都暗中为父亲的骨气而感动,同时也为他的前途担忧。
黎明前的最后一搏
1976年是一个转折之年。随着「四人帮」的垮台,社会气氛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。虽然「两个凡是」还笼罩着思想界,但敏感的人已经感受到了变化的气息。
就在这个时候,父亲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决定。在政协的一次会议上,他再次主动要求发言。
当时会场里很多人都还记得他20多年前那次著名的争论,所以当主持人宣布他发言时,整个会场都安静下来,所有人都想听听这个老人又要说些什么。
父亲慢慢站起身来,环视了一圈会场,然后开口说道:「同志们,刚刚结束的这场运动,我觉得有必要实事求是地进行总结。」
会场里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。要知道,当时还没有人敢公开对刚刚结束的那场运动进行全面否定。
父亲继续说:「这场运动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巨大损失,这是不争的事实。究其根本原因,就是我们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,过分依赖个人权威,而忽视了法律制度的建设。简单地说,就是人治代替了法治。」
「历史已经多次证明,任何个人都不可能永远正确。如果把国家的命运完全寄托在某个人身上,而不是建立起完善的法律制度,那迟早会出问题的。这次的教训,我们必须认真吸取。」
这番话说完后,会场里静得连呼吸声都能听到。许多人都被父亲的勇气所震撼,同时也为他的大胆担心不已。
但这一次,时代已经不同了。父亲的这番话虽然超前,但并没有引来新的麻烦。相反,随着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兴起,他的观点渐渐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同。
晚年的荣光
1979年初,全国第五届政协会议在北京召开。邓小平当选为全国政协主席,而父亲也被选为政协常委。这对于一个曾经被批判了20多年的老人来说,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转折。
在这次会议上,已经85岁高龄的父亲再次成为焦点人物。当他被介绍上台时,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。许多人都是第一次近距离看到这位传奇老人,都被他的风度和气质所感染。
在随后的发言中,父亲再次展现了他的风骨。他说:「经过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,我更加深信一个道理:真理是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改变的,正义也不会因为暂时的挫折而消失。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太多的苦难,但也见证了真理的力量。希望年轻一代能够从我们的经历中吸取教训,坚持走正确的道路。」
这番话赢得了经久不息的掌声。许多在场的老同志都流下了眼泪,他们想起了自己在那些艰难岁月里的遭遇,想起了那些为了真理而付出代价的朋友们。
会后,许多人主动来找父亲交流。其中不少是当年批判过他的人,现在都诚恳地向他道歉。父亲总是淡然一笑:「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,重要的是我们要向前看。」
10个月后,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,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。父亲也被任命为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,终于迎来了自己人生的春天。
永恒的精神遗产
1988年6月23日,95岁高龄的父亲平静地走完了自己的人生路程。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,我握着他的手,看着他安详的面容,心中涌起千般感慨。
父亲走后,我和哥哥开始整理他留下的大量资料。在那些厚厚的日记本里,我们看到了一个知识分子在时代风浪中的坚守与挣扎,看到了一个普通人在面对巨大压力时的勇气与智慧。
有人曾经说过,一个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的知识分子很难保持内心的平静,他们往往会愤怒、忧伤、痛苦,这些情绪常常会损害他们的身心健康,甚至影响寿命。但父亲却是个例外,他一生都在为理想而战,却又能活到95岁的高龄,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。
我想,这个奇迹的秘密就在于父亲内心的那份坚定和豁达。无论外界如何变化,无论遭遇多大的挫折,他都能保持内心的平静和对真理的信念。正如他在日记中写的那样:「道路虽然遥远,但只要走下去就能到达;事情虽然困难,但只要做下去就能成功。人的生命有限,但真理是无穷的,虽然我们不可能达到完美,但我们的心永远向往着真理。」
现在,当我翻阅着父亲留下的这些珍贵资料时,我深深地感到,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记录,更是一个时代的见证。它告诉我们,在任何时候,人都不能失去对真理的追求,不能放弃内心的坚持。这或许就是父亲留给我们这个时代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吧。
658金融网配资-配资平台查询官网-查配资炒股-战略杠杆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